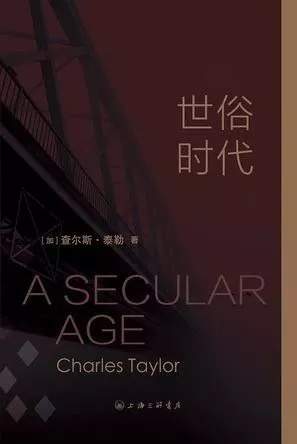德国对小孩的教育方式(德国在儿童方面的政策)
21世纪的社会治安好转了很多,小康社会日益成真的时代,充斥公共场所和社交媒体的,似乎都已经转移到熊孩子身上了。无处不在的熊孩子,以及他们的老年版——那些被称作“坏人变老”的一代,和熊孩子们在公共场所的肆意吵闹类似,也会在公共场所肆意伸出咸猪手、霸占座位、随地吐痰、辱骂他人、裸露生殖器等等。
只要环境不变,这些熊孩子和年老版的互相参照,待他们长大,就会发育成为精致版的熊孩子,弥漫整个世界。对此种未来,新兴中产阶级除了忧虑和不能忍,好像并无办法,连所谓“贵族学校”都可能是熊孩子的生产机器。
不过,在熊孩子们最终占领星球之前,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没有熊孩子的天堂”,那就是欧洲,尤其德国。那里不止生产甲壳虫汽车、Rimowa和儿童绘本,还堪称没有熊孩子的国度,可以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父母们提供一个教养的范本。
譬如说,在德国的公车中部,也是停放婴儿车的位置,随着公车停靠上下,常能看到德国小孩和土耳其小孩、阿拉伯小孩以及非洲小孩共处平行的场景。然后,最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这些外国小孩们在婴儿车里哇哇大哭,需要父母不停安抚,而德国小孩往往就和周边乘客一样安之若素,继续瞪大眼睛瞧着婴儿车顶的玩具。这一情景无关任何种族主义,只是多年来个人的直接观察结果,也为许多朋友的观察所证实。
类似的,如果造访当地朋友,遇到抚养婴儿的家庭,也无数次重复着几乎完全相同的一个情景:不足岁的婴儿被放在婴儿房的地上,当然地上铺着一张毛茸茸的羊皮毯,婴儿一个人安静地望着头顶婴儿架上的玩具,父母则在另一间的书房工作,互不干扰。
每年探望这些朋友家庭,谈的话题自然也离不开孩子,诸如托儿所和幼儿园问题、政府的儿童补贴金、难民危机后的幼儿园吃猪肉问题、上学小孩路上安全问题等等。这些德国家庭的孩子也要忙于各种滑雪、舞蹈、钢琴课,还有额外的中文课,可是一年年就保持着安静、活泼、和教养,在中产阶级父母的抚养下长大,时刻准备着脱离家庭,融入社会。我还有一些来自德国上流社会和半失业的朋友,如果比较他们的孩子气质和家庭抚养,几乎看不出阶级差别。
然后,在德国社会,日常生活和公共场所几乎找不到所谓熊孩子。在公车、火车和几乎所有公共场所,人们总是轻声低语,见面打招呼,进出留门。绝大多数人日常穿着也极尽朴素,一眼望去灰黑蓝。
例外的情形也有,就是每年狂欢节或者啤酒节的时候,那可能是德国人民最放浪形骸的季节了,火车站变得和伦敦的周末街头一般,躺满喝醉酒的男女青年,也是每年强奸案、抢劫案发案率最高的几天。平素日子里,严肃的德国人也只有在天体海滩上展现快乐的一面,那是忍受每年复活节假期或者暑期高速公路爆堵塞车后换得的自由。
偶然入耳一片喧哗,不用抬头就知道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偶见花枝招展跟环境不搭的也多半来自中国。就像国内的情形,公共场所无一不处于严重噪音污染中,总有人在地铁车厢上旁若无人地放声看视频、长时间打电话、吃包子;上下电梯难得遇到耐心等候或者留门的,总是不停地按关门键;街道和公车、地铁一样,总是被高分贝的音乐声、广告声占领。更有一次在健身房,我向旁边的跑步机用户抱怨,希望调低机前电视的声音,说“这不是家里”,得到的回答却是:有什么区别吗?无语的我只能暂时离开,默默举铁。
通常看来,这一分别,只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群己权界上的差异,包括对身体安全距离的感知差异,或者对隐私概念和公共性的认知差异,就像大多数中国人永远喜欢唐人街的喧嚣,这似乎也是广场舞的正当性的心理基础。这种差异,也很容易被归为国民性或者国民素质的差异,尽管所谓国民性(特征)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在一个世纪前流行,也同样容易被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否定。
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国民对于自我身体的感知和控制,如同福柯所强调的身体规训问题,却伴随着启蒙时代以来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也就是查尔斯·泰勒的名著《世俗时代》所努力揭示的,身体的浮现,与新教伦理一道扮演着世俗时代形成的关键,它联结着个体和整体,也联结着基督徒的生活和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想象。
而所谓熊孩子现象,理论上说就是轻微的逾矩行为,尤其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却如同那些在公车上啼哭的婴儿,仍然停留在肛欲-啼哭的反应模式中,仿佛永远没有断掉的脐带,在父母的庇(溺)护(爱)下为所欲为,并没有准备融入现代社会以陌生人团结为中心的道德体系。这通常是各国轻微犯罪法庭对付的问题,对屡次违反的青少年——熊孩子通常以感化院、教养所、工读学校来矫治。而有意识的群体逾矩,则是社会运动或社会抗议的范畴,他们以故意冲撞社会秩序来挑战社会主流意识,促进社会变革。
只是,在中国,没有轻罪法庭,工读学校和劳教制度也取消了,很多熊孩子的自觉不自觉破坏也够不了治安处罚,加上警察无心搭理或无力处置熊孩子的破坏,他们被视为家庭(间的)行为。公共秩序只是中产阶级的奢望,他们也没有办法对付属于自身阶级的熊孩子在公共场所的捣乱。
所以,如果从反例——没有熊孩子的德国细究下去,就能发现熊孩子所涉及的不仅教养问题,在德国还以另一种非常特殊、近乎民族特征也就是国民文化养成的方式体现出来,影响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教育体制、和社会类型。
教养
所谓教养,大概是中国人民最近几年最为关心的一个词了,似乎所有的社会新闻都围绕着教养在打转。一切的社会冲突、阶级认同、婚姻问题等等,都被归结为教养。只是,奇怪的,至今还没有围绕教养滋生出一个新的产业。人们似乎也只是简单地把教养等同于教育,对学区房的争夺也因而代替了一切。
这不奇怪,新鲜的中产阶级自身还在迷茫,夹在各种小的、老的熊孩子中间,并不知道如何真正地教养孩子,有的干脆把责任推给学校,或者只是想把孩子送往海外上高中,更有理想主义的最多把孩子送到打着华德福招牌的学校,全然不知中国的各色田园华德福已经在教授国学,和华德福的自然教育理念根本相悖。
而教养的本义是parenting,泛指父母养育,在传统阶级社会中,教养几乎就是绅士阶级养成和阶级再生产的代名词,特别是礼仪行止、阅读交谈、见识气质和价值观等,与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口音和古典修养等相得益彰。但在现代公民社会的背景下,教养很大程度上与公民教育有关。
不止是现代公立教育体制承担公民教育的责任,传统属于私领域的家庭也同样需要在教养中践行公民教育,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和融合问题上,也会反映在暴发户为得到主流社会承认所面临的障碍,例如购买超出自身负担能力的豪华房屋或者奢侈品就会被认为缺乏教养。
在德国,教养的标准已经融为国民标准,包含了一些传统被认为属于德国国民性的特征,如秩序、守时、清洁、节约、能干、勤奋、严肃、彻底、职责、忠诚和正直、保护和捍卫、热忱、单纯等。其中,有些源自骑士精神,有些源自新教伦理,还有些源自德国近代思想浪潮对古希腊文明的憧憬。
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的“礼、智、勇、仁、信”到今天几乎被人淡忘,这些早熟的道德标准并未完成它们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继承,也未能变成今天中国人-熊孩子的行为规范。而德国的这些道德标准,都不同程度地曾被德国的著名诗人、文学家、知识分子推崇、赞美过,而融入德国文化传统,成为每个家庭教养子女的准绳。
例如,1901年出版的《妇女当家庭医生》(Die Frau als Hausartztin),初版800多页,甫问世就成为畅销书,也是德国中产家庭的常备手册,到1913年销量突破100万,且不断修订,篇幅增加到1000页,最后一版一直印到1993年才告结束,总销量336万册。这本家庭医生手册,涵盖女性和青少年的身体、生理、生殖、卫生、清洁、疾病等等几乎所有身体卫生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初版也早早涉及了青少年手淫等性问题,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未免保守,但在当时已经很是开明、医学化了,而且屡经修订。
作者安娜·费雪-杜克尔曼,作为军医的女儿,是德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和执业医师,第一次以女性卫生的角度详尽教导家庭和妇女如何培养儿童的成长,从洗澡洗衣到疾病护理,甚至包括如何矫正儿童读书坐姿的细致插图。这些都是教养的内容,犹如小时候家父母总是提醒我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绝对容不得葛优瘫,而且白天不能沾床、早晨起床一定要自己整理内务等等。这本家庭妇女治理家政的“黄金宝典”,因此堪称现代德国以身体为中心的家庭教育的先驱,大大提高了女性地位和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然后扩散到所有德国家庭的普遍教养水平。
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也许最好反映了德国社会为进入现代化也就是朝向世俗时代转型的准备,其意义不次于一场大革命前的准备,如考茨基曾经所说,不是准备革命,而是为革命而准备。
事实上,在泰勒的《世俗时代》——这本关于现代性的大学必读书里,过去500年从宗教生活向世俗生活的转变正是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始作俑者是马丁·路德,连同随后跟进的加尔文,他们共同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宗教改革重新定义了社会秩序的目标,不再是跟随上帝的方式,而是人间福祉,追求秩序的力量也不再从上帝支取,而是依靠属人的能力,也就是从因信称义出发衍生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催生了洛克、格罗秀斯等等对政治秩序的想象,尤其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隐喻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的关联想象。
而那些清洁、严肃、能干、严谨等等19世纪以来德国国民性的建构,正是路德以来德国宗教革命所唤起的个人主义和知识分子如康德对道德社会的秩序想象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在今年,也是路德在维滕堡教堂贴出“九十五论纲”500周年之际,重温这条从路德到康德的转型之路,或许才是了解一个“没有熊孩子的天堂”的最好方式。
路德张贴论纲的大门
Bildung
其实,这些关键词中,如“能干”(Tüchtigkeit),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含义,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德国朗氏法语字典把它译成“一个人所具有一切所需的能力”(qui a toutes les qualités requises),而朗氏的《英语学生大词典》中根本就不译,只是列举了一堆近似词,如capable, efficient, competent, qualified, clever, skillful, proficient, experienced, excellent等等。而在德语语境中,能干和美德(Tugend)词源相同,兼具伦理价值,包含对一个人出色才干的肯定,个人的表现也就同时具有了社会评判的意义和关联。
与此类似,德国的教养概念体系中有一个最为核心却也是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因此不具普世性的,是Bildung。它不同于教育education,或padagogy, 可能是德语中一个最难以捉摸、却最有德国文化特色、也能代表德国制度真实的概念。譬如,加上前缀Aus构成的Ausbildung,是泛称学历教育的意思,德语口语中的常用词,却可以包含中文语境下学历教育之外的自学和其他学习方式。
尽管德国有着世界上可能最为严格的法律(例如一部在纳粹时期通过的专门法律至今有效,禁止德国以外获得的博士在德国自称博士),但是有些政客还是设法通过函授和抄袭获得文凭,后者一经查出就身败名裂。不过,最励志的莫属前社民党总理施罗德,虽然早早就因家境原因脱离了学历教育而分流在职业教育轨道,但是18岁后干着地盘工人和销售职员的同时坚持上夜校,1966年22岁时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取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的资格,十年后通过了第二次法律国家考试,开始了律师尔后政客生涯。
施罗德如此漫长的学习,堪称 Bildung理念的化身,也能代表典型德国人的成长历程,特别是那许多在大学里一泡就是十几年的学生,社会对大学生的宽容和优待也来源于此,仿佛德国哲学家阿尔多诺的解释:Bildung就是让等待成为可能。这不就是最契合资本主义的“迂回生产”精神吗?只有足够陈酿的葡萄酒和威士忌才能卖出好价钱,注入工匠精神的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也如此,连德国的职业培训制度甚至劳资集体谈判也遵守这一精神。
对德国人来说,在教养的意义上,Bildung是有着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它包含着个人应当努力去完善自我的目标。换言之,它不同于通常的教育,因为它是不可见的、严格个人化的,意味着一种异质性的教育,而非标准化的、可以客观标准衡量的教育。也与通常的父母和教师教育相反,这些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的工作多少都是可替代的,可以由他人取代。
字面上,Bildung则是不可替代的,英语世界也只能照搬,还有一系列英文的近义词,如formation, growth, shape, training, education, culture,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culture, refinement, good breeding等等,合适的中文意思也许是“养成”,意味着在教养和教育的同时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天赋进行自我完善。在德国,这种教育理念被认为是塑造所有人道德标准的传统智慧,也塑造杜克海姆所说的社会化方法(socialisation methodique),而构成社会的支柱。贯穿了从17世纪到洪堡教育模式再到今天的德国教育的核心,也是真正的华德福式自然教育方式所秉持的,按照人的天性自然发展,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够成为不一样的人,也是充分发展的“能干”的人,兼具个人主义和道德义务。
或许,德国这一关于人的发展的理念,才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来源。事实上,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型本来就源于新教衍生的与共济会、烧炭党类似的、前身为在日耳曼移民劳工基础上形成的日耳曼大众社的正义者联盟。而历史进程中的Bildung,也正是从过去500年的新教革命引发的社会变革基础上一步步演变而成。
对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在实用和享受的区别上,奥古斯丁把Bildung归为享受一边,区别于实用。 Bildung-养成教育是对它自身价值的肯定,而非为了实用或功利的目的,13世纪建立的方济各会的托钵僧们也始终践行这一神学修养的原则。至今仍然在德国偶尔看到年轻的芳济各行游僧人,他们要独自在工地或者农田一边打零工,一边传道,像黑森武士一般度过若干年这样的苦修,才能完成学业。
方济各会修士
这种漫游、独自苦修的方式和传统经院不同,跨越了现有社会领域和秩序空间,恍如另一种中国人眼中的“熊孩子”,却孕育了14-15世纪大批出色的神学家,包括兄弟教会道明会的阿奎那,也与德国的漫游传统相契合。慕尼黑的今天还有古老的芳济各啤酒,而Bildung的个人养成教育传统也保留下来。
譬如说日耳曼人森林流浪传统衍生出的流浪武士,在地中海国家充当雇佣兵,功成名就者就跻身骑士和年轻贵族,形成近代德国史上最重要的容克阶级,塑造了普鲁士军事传统,堪称另一种Bildung-养成教育的典范。在海外,他们还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双方,也是战后法国海外军团的主力,参加了奠边府战役,至今仍然是梵蒂冈瑞士军团的主要兵员。
不过,将这种个人的学习推广到所有人,特别是普通德国人,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功劳。新教的核心是神恩和敬虔,信徒与上帝间的“因信称义”的直接沟通,代替了传统家庭和共同体的脐带联系,也产生了世俗社会中一种新的平等和团结的可能,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模式。虽然他一方面在诸如《加拉太书注释》里借保罗之口否定世俗律法的重要性,认为单单遵守外在的品行并不能成为基督教,但是在1521-25年农民革命中转向维护世俗权威和秩序。在1524年的动乱时局中,路德从维滕堡写信给德国各城市建立学校的委员会,“对男孩和女孩来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世界需要善良的和能干的男女从外部来维护世俗地位,这样才能帮助公平地统治国家和人民,妇女也才能教育子女和仆人并维持家庭”。
在欧洲中世纪的转折点,第一次,由路德强调了对所有人特别是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教育、家庭和秩序就这样从路德开始,成为新教对社会的想象,开启了一个世俗时代的转型。
远在日内瓦的加尔文更为政治化和积极,但对这个德语词并无多少体认。他所坚持的,如在《基督徒生活的黄金手册》中,是关于基督徒的敬虔即盼望永生是会产生正直行为的,呼吁信徒们节俭生活。这种加尔文主义对信徒个人的永世默想的推崇,当遇到大航海时代将大自然带入人类的道德想象后,如泰勒所说,从不同方面改变了我们。这可以解释美国西部荒原对新教徒的震撼,也同样可以解释一个自然科学时代的开启对德国民众心智的重塑和对新秩序的想象。
其后,如路德所愿——他被1525年起义的农民批评为“诸侯的宗教”而不是“人民的宗教”(路德本来就因得到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而免于教廷的惩罚),宗教改革所引发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最终促成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现代世俗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然后,一切新的概念和方法,无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算计,还是配第的经济计算,或者哥白尼的革命发现、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康德的理性研究,终于在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浪潮下相继涌现,代替了陈腐的宗教语言和幽暗的时间维度。只是,加尔文主义的美国新教徒只有到1928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向他们揭示了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那种充分自由发展的可能之后,才意识到德国式养成的自由。
而在德国近代前两百年,德国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时代,这种自由发展的养成教育继承了“基督教要占据内心”的教诲,不是侧重发展个人能力,而是如当时德国哲学对整体性的强调,把个体当作集体的单位,注重从经典中培养“内心的提高和贵族意识”(洪堡语),对新兴科学的态度也是融入生命,强调研究和学习的统一。这也是洪堡大学模式的精髓,追求在近代科学体系中完善自我。
应该说,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过去数十年对科学、知识和生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而且很好契合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儒家心学,颇有一丝现代主义早期的科学神秘主义感觉,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很容易被当作异端来对待,如同加尔文在日内瓦为维护城邦的威权做法。其实,现代社会控制的原则也产生于这一阶段,如同亚当·斯密的神秘主义解释,当个人的最大化追求和社会的整体目标一致时,就达到了最优的社会控制。如果熊孩子们都在努力创业、挣钱、消费、还房贷,那么也就没有熊孩子了。这不正是中产阶级对自由主义的秩序梦想吗?
也是从19世纪初开始,普鲁士首先建立了政治警察,形成警察科学,一个以法制和警察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建立起来,随着德国统一和民族主义上升逐渐控制了德国社会,也系统消灭了各种逾矩群体。城市暴力形态只剩下零星犯罪和国家暴力,纳粹和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过是其延伸。在今天的公共场所,可以见到各种控制力量,警察、佩枪的地铁保安和城市秩序办公室的人员,随时干预任何熊孩子似的逾矩行为,特别是那些中国街头常见的成人打架、当街便溺等。以致于,连火车站周边的流浪者也都颇有尊严,或者卖艺,或者礼貌安静地行乞、等待救助机构的每天施粥。
而1860年之后德国Bildung概念和实践的发展,如同这个充满技术革命、科学霸权和人类冲突和混乱的百年,残留的养成教育以新历史主义方法反抗这种科学主义霸权,也反抗科学主义霸权下教育普及和官僚体制的发展对时代精神的改变。养成也逐渐在人类的灾难和反思中获得了更多的批评能力,不仅以公开抗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如同“我们潜在的鲜活记忆的存在赋予我们的行动和经验以意义”。这就是战后的1960年代中期以后Bildung – 养成意识的复兴,要求超越日常生活和目的需要,与现实生活的必需要素反向而行。
著名社会学家达伦道夫1965年特别声明,Bildung-养成是一项公民权利。这在68革命后成为现实,高等教育改革开始,教授们开始创办自己的大学,如比勒菲尔德改革大学,那所大学的创始教授正是新历史主义学派代表和控制论理论家。德国大学反而成为 Bildung-养成范式的大本营,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初其比例一直稳定在18-25%之间。而68革命一代的学生,那可能是在中国人眼里德国战后唯一算得上“熊孩子”的群体,在新的养成体制下也转型为丰富的新社会运动,一种群体性的旧秩序挑战者和新秩序创造者。
勒菲尔德改革大学
养成,也回到了最初的目的和实践合一的行游僧模式。毕竟,德国虽然有着新教国家的称呼,但是今天的天主教信徒规模却超过新教,19世纪以来新托马斯主义的发展早已经大大丰富和扩展了德国对个人养成、对社会秩序的态度和想象,区别于新教大陆,也以古老的苦修传统继续示范着普通人如何在世俗时代以这种异化、带着神学色彩的术语——Bildung,在纷杂的社会化空间里“保持学习和人类经验的自治”,而努力趋向德国哲学如贝克在全球化时代向国民示范的个体主义社会的可能,如何维持一个负责任的个体学习和性格养成的范式。
在这样一种养成模式下,任何宗教争论或者阶级冲突都显得无关紧要,都不成为社会生产和容忍熊孩子的理由。剩下的只有零星犯罪和拒绝养成教育而仍然停留在肛欲-啼哭模式的“巨婴”族群,后者仍然停留在前现代的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伦理中,据说还要继续发扬光大,然后他们的扩张恐怕是不仅德国、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胁。